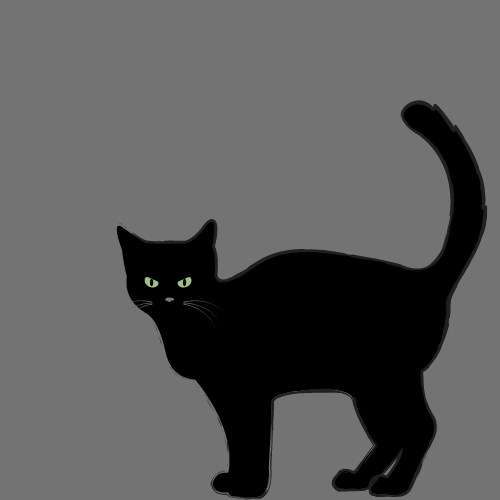书摘-《可能性的艺术》
《可能性的艺术》-刘瑜
事实上,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、民主、和平,很多时候,人们更渴望的,可能是安全,是秩序,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。
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。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,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。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、正常的甚至必然的。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,希望它变得更好,但是却没有意识到,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。
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,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,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。
如果你觉得“万众一心”是好事,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,001个声音。
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,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。
未来如何确定无疑,但是过去怎样,却难以预测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,它不容置疑,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,却不好说了,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,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。
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。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。
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,面临着两大难题: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,也就是“谁当猴王”的问题;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,也就是“猴群的势力范围”问题。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,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。
这个世界上,比悲惨更可怕的,是不为人知的悲惨。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,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。
很大程度上,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。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,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,他们只是恪尽职守,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,但是,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,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,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。
什么叫“理性的无知”?意思就是,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,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。特定情境下,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、无法改变、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,因为“知道”会唤醒良知,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,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,不如什么都不知道。
所以,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?因为恐惧,因为利益诱惑,因为观念的魔法。个体的恶或许乏味,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,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,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。
本文标题:书摘-《可能性的艺术》
文章作者:Leung VanGi
发布时间:2024-07-21
最后更新:2024-07-21
版权声明:本博客所有文章除特别声明外,均采用 CC BY-NC-SA 3.0 CN 许可协议。转载请注明出处!